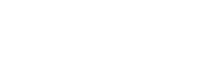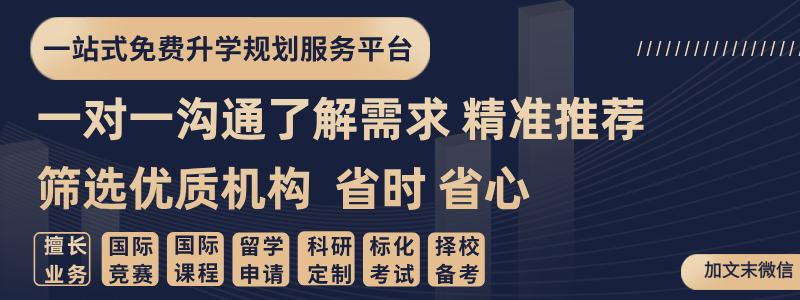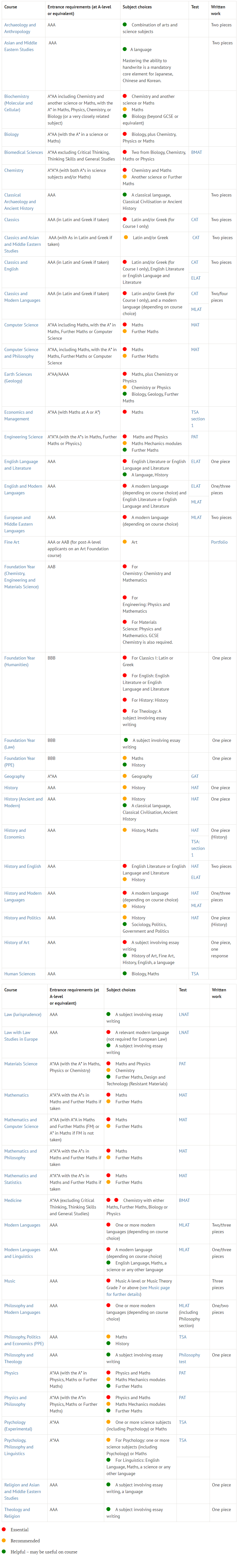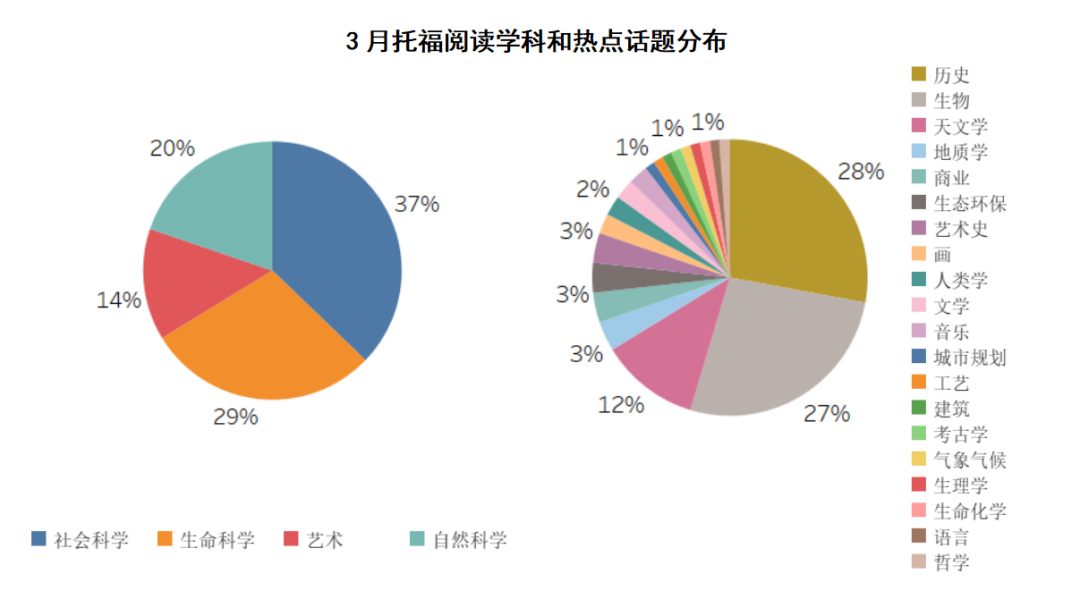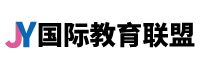在我担任马卡莱斯特学院校长的17 年任期中,大约有四年时间,我会见了我们学术与教学中心的主任。她几乎可以肯定是校园里最受人尊敬的教员,几乎样样精通,并为学院的进步不遗余力。
她有一种在任何大学社区都难得一见的品质:在同事中几乎具有普遍的威信。我们谈话的主题是她工作的两个重点:学术和教学之间的关系。
她花了很大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在仔细研究了教学评价等内部证据和更大数据集的外部研究之后,她得出结论:事实上,传统的研究成果与课堂效率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后来多次得到证实)。这当然是个大问题,因为人们,尤其是像马卡莱斯特这样的研究密集型文理学院,都坚信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卓越的教学效果是相辅相成的。
这一信念贯穿于从招聘到终身教职决定再到加薪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学院描述和思考自身的核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在学院内部进行更广泛讨论的话题,具有足够的兴趣和重要性。
我们都不期望迅速或戏剧性的变化,但任何改进的第一步似乎都是考虑证据。我们安排了一次自愿参加的全体会议,在会上,主任将介绍她的一些发现并引导讨论:
在马卡莱斯特,对学术生产力的期望是否已经发展到扭曲了我们未终身教职和部分终身教职教师的专业发展,并与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其他利益--如教学、指导和课程开发--背道而驰的地步?我们是否更接近于大学模式,而远离了教学/学术/服务平衡的文理学院模式?
毫不奇怪: 事情并不顺利。全体会议上的反应大多是敌意的,尽管没有随后在电子邮件或走廊里的评论那么敌意。一位教师指责我试图"把马卡莱斯特变成幼儿园"。
即使是那些对调查结果不那么敌视的人,也对其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不仅是对变革的抵触: 对谈论变革也有抵触情绪。许多教职员工认为,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学院价值观的攻击。
经过几周的激烈反驳,我和院长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这不值得。考虑到管理学院和服务学生的日常压力,我们根本没有精力参与这场很可能激怒教职员工并最终一事无成的辩论。
如果维持现状是我们的目标,那么高等教育就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系统。
我之所以要详述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因为通过忽视相关研究来捍卫研究的作用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做法,还因为它体现了高等教育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任何类似严肃变革的抵制都是深刻的。我所说的"变革"并不是指增加一个项目或改变一个毕业要求,而是指那些具有变革性的、在深层次上影响我们工作方式的变革。
康奈尔大学英语系更名为 "英语文学系"的决定引发了争议。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公布的2022年 "最具创新力"大学前十名中,不乏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Stanford)和普渡大学(Purdue)这样的激进分子。
几乎所有的管理者或教职员工,只要一开始就有转型变革的想法,最终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这不值得。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由自认为政治上自由的人广泛参与的行业,在其自身工作方面却如此保守;为什么学科不断发展的学者们却如此抵制机构的发展;为什么几乎总是在其使命宣言中谈论教育变革力量的高校,却发现自己的变革如此困难;为什么几十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中几乎没有任何基本实践--日程表、终身教职程序、教学法、评分--发生过有意义的改变。
这些问题经常被问及,但最常见的答案却并不充分。教师们倾向于责怪官僚主义的管理者;管理者倾向于责怪顽固不化的教师;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之外的人倾向于责怪几乎所有与高等教育机构有关的人。
答案往往在于高等教育内部形成的结构、实践和文化。如果维持现状是我们的目标,那么高等教育就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系统。长期以来,是什么阻碍了高等教育的转型变革?为什么即使是苟延残喘的机构也无法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对此有什么办法吗?真正的变革显然是必要的。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列出的近4,000 所两年制和四年制中学后教育机构中,也许有100 所可以说基本不受当前和未来市场压力的影响。
其余的院校在财务和教育模式上都面临着挑战,这些挑战在种类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在严重程度上却惊人地相似。经济挑战可以用复杂或简单的术语来解释。由于我的专业是英语教授,所以我选择简单。
1. 传统学院或大学提供服务的成本非常高,几十年来,其增长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或生活费用指数。
2. 除极少数拥有巨额捐赠的院校外,其他院校的大部分成本都来自学生的收入。
3. 没有足够的学生愿意并有能力支付高等教育的全部费用。
4. 没有足够的学生,仅此而已。抛开所有的图表和经济数据,问题很简单: 当你所提供的服务成本超过了人们愿意和能够支付的费用,当你无法降低服务成本,当你的潜在客户数量不断减少时,你的财务模式就可能是不可持续的。高校通常以两种方式应对财务压力:削减开支和降低价格。
让我们来看看削减的方法,它通常遵循一个模板:"经济和人口的逆风十分强劲;我们正在积极行动,使我们的学院/大学在财务上更具可持续性;尽管我们将以更少的人提供更少的东西,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善学生的体验;我们并没有--真真切切地--处于财务拮据的状态"。我理解有必要提出这样的说法,但这样的说法可能会导致推理上的扭曲,而这种扭曲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明尼苏达圣玛丽大学--高风险院校的典型代表--在 2022 年宣布取消 11个专业和 13 名全职教师,并在声明中自问自答:"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们如何才能让学生为工作、为有道德的服务生活做好最好的准备,在回答他们关于意义和目的的问题的同时,追求更大的利益和万事万物的真理?"受影响的课程包括英语、历史、音乐和(是的)神学。今后的重点将放在商业、技术和自然科学上。
至少可以说,这是为学生的意义和服务生活做准备的一种新颖方式,尽管听起来比事实更容易接受:我们希望通过将资源从艺术和人文学科转移到商业、科技和科学领域,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一席之地。
2014 年,深陷债务危机的俄亥俄州海拉姆学院取消了艺术史、音乐、哲学和宗教专业,增加了体育管理和国际研究专业。该校将这种做法称为"新文科"。或者,我应该说,新文科™。读者,他们把它注册为商标了。
即使是很小的削减也会引起巨大的反响。
校园和校友对这些削减的反应就像公告一样公式化:震惊、悲痛、愤怒、抗议。有时是投不信任票,有时是威胁扣留所有捐款。当遇到这种完全可以预见的反应时,削减的数额会减少或完全撤销,让人不禁要问,这些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反应。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斯角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Stevens Point)在2018 年宣布了一项取消13 个专业的计划,成为全国性新闻。戏剧性的一幕接踵而至。在将拟议取消的专业数量减少到6 个之后,斯蒂文斯波特大学最终取消了......
一个也没有取消--这既没有解决长期的预算挑战,也没有完全安抚社区,社区仍然对当初提出该计划感到愤怒。
圣玛丽大学和斯蒂文斯波因特大学宣布的削减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即使是很小的削减也会引起很大的反响。2003年秋天,当我来到马卡莱斯特大学时,该校是中西部少数几个拥有北欧滑雪校队的大学之一,尽管该队的队员人数很少(我相信只有九人),而且维持费用非常昂贵。
根据一位担心预算的体育主管的建议,我宣布北欧滑雪将转为"俱乐部运动",考虑到其规模和成本,这样的身份更为合适。换句话说,这甚至不是削减,而更像是降级。这一消息不仅激怒了马卡莱斯特大学校园,就我所知,还激怒了整个美国北欧滑雪界。三百封电子邮件之后,我被指控破坏美国北欧滑雪运动,威胁马卡莱斯特作为文理学院的地位。(试想一下,如果2003 年就有Twitter、Facebook和Change.org,我的总统任期将会非常短暂。我的校长任期将会非常短暂)。
我确实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我也早早地领悟到,要想从大学社区夺走任何东西都是很困难的。如果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财务挑战神奇般地消失了,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考虑转型变革。
事实上,高等教育界需要变革的最有力的理由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教学方面的。高等教育仍在不经认真反思的情况下依赖于太多我们已知相对无效的做法,而这些做法在肾脏学和放血术流行的时候就已经很普遍了。
正如乔纳森-齐默尔曼(Jonathan Zimmerman)写道:"自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时代以来,大学教学的变化可能比美国几乎任何其他机构的做法都要少。举例来说,讲课已经统治课堂数百年之久。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斯科特-弗里曼(Scott Freeman)将讲课的历史追溯到1050 年,当时西欧的大学刚刚成立。
有大量证据表明,讲课是一种无效的教学方式,而且无可争辩。正如"翻转课堂"的先驱之一、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埃里克-马祖尔(Eric Mazur)所说:"这几乎是不道德的:"然而,在大大小小的教室里,面对面或通过Zoom 进行的讲座仍然非常普遍。对 200 多项有关本科生STEM 教学方法的研究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将学生变为主动参与者而非被动听众的方法降低了不及格率,并将考试成绩提高了近二分之一个标准差"。
换句话说,"做中学"比 "听中学"更有效。我不会说讲课应该突然完全消失,但这个话题难道不值得至少召开一两次教师会议吗?2012 年,《哈佛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马祖尔的文章,以"讲座的黄昏"为题,颇为乐观地阐述了反对讲座形式的理由。十多年后的今天,太阳离落山已经不远了。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需要更新的特点是教学日历。
在我作为学生、教师和管理者的几十年中,我曾与六所高校有过联系,在每所高校,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全力以赴地开展中心工作--教学生(公平地说,许多两年制院校和一些四年制院校的情况并非如此)。(公平地说,许多两年制院校和一些四年制院校的情况并非如此)。
还有哪个重要行业是这样的呢?试想一下,如果医院、超市或邮政服务在1 月份暂停,6 月到 8 月又暂停,那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七月中旬,我走进马卡莱斯特耗资5000 万美元的艺术综合楼,发现灯关着,空调开着,有时楼里一个人也没有,这种奇怪的感觉一直让我难以忘怀。偶尔,我也会遇到一个在办公室工作的教师,或者一小群参加暑期艺术项目的中学生。
我们耗资4000 万美元的娱乐中心在暑假期间被用来举办拉拉队训练营和体育学院等活动,但这些活动从未有马卡莱斯特的学生参与,带来的收入也微乎其微。我想不出还有哪个行业会如此低效地使用昂贵的物质设施。
该行业需要改变的最有力的理由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教学上的。
因为对大多数大学来说,暑假停课三个月是不够的,许多大学还需要放一个长长的寒假。在马卡莱斯特,学生从12 月中旬到 1 月下旬放假。从前,这个假期是用来上J 期课程的,但在20 世纪 90 年代初,教职员投票决定取消这些课程,但他们当时选择--从那以后也一直选择--不改变由他们控制的校历。
其结果是,每年授课时间不足30 周,仅够达到认证的最低要求。中断教学为研究服务通常有两个理由。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因此,教职员工要履行两种职责:教授学生和通过创造知识推动社会进步。
这一论点在涉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时很有说服力,但应用到大多数人文学科领域时,它的基础就不稳固了。尽管我很努力,但我无法说服自己,因为我出版了一本关于狄更斯的《小杜丽》的书,世界就变得更美好了--尽管它确实帮助我获得了晋升--我也无法说服自己,写那本书比教我的学生写作、仔细阅读和欣赏文学的力量对社会更有价值。
第二个理由是,有成就的学者可以成为更好的教师。教师有优秀的,也有不优秀的;学者有优秀的,也有不优秀的。这些类别并不以任何容易预测的方式重叠,但在最精英的高校,甚至在许多并不那么精英的高校,我们只是假装它们重叠了。
反对典型日程表的最有力论据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教育方面的。要降低四年制大学学位的成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其改为三年制大学学位,而这一点可以通过延长学年来轻松实现。无论是四年制学位还是120 个学分的要求,都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两者更多的是基于传统,而不是基于有效性的证据,而且在英国、德国和非洲部分地区,这两者都不是标准。
我们可以说,学分要求是与对广度和深度的期望联系在一起的,至少在通识教育中是这样,但更难说的是,这些学分必须分散在四年的时间里,中间要有较长的休息时间。以前尝试提供三年制学位时,既遭到了教师的抵制,因为他们担心学术严谨性,也遭到了学生的抵制,因为他们似乎想要完整的四年大学生活。
最近,由罗伯特-泽姆斯基(Robert Zemsky)和洛里-卡雷尔(Lori Carrell)领导的一个名为"大学三年制"(College in 3)的项目正在与13 所院校合作,试行三年制学位,但现在要确定学费的上涨是否会增加缩短完成学业时间的吸引力,或者这项努力是否会得到教师、学生或首席财务官的广泛支持,还为时尚早。迄今为止,有证据表明,与"新常态"相比,高校更倾向于"旧常态",并正在竭尽所能回归"新常态"。
许多较为稳妥的院校的普遍态度似乎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经济学家迪克-斯塔茨(Dick Startz)的观点相似:从长远来看,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渴望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此需求会恢复正常。提供高等教育的成本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供应也将恢复正常。在线教学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利基产品,但就大多数目的而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更有优势。
再过几年,大学的财务状况应该会恢复到往常的状态,至少可以勉强维持。"至少过得去":不太鼓舞人心,而且对于越来越多的大学而言,中长期前景堪忧。关于需求,Startz似乎错了,除非名校的需求增加而其他学校的需求减少被认为是"正常现象",但在财务模式(变化不大)和教学模式方面,他似乎更接近正确。
传统学院更倾向于将"大流行病"时期视为一种中断,而不是一种永久性的方向转变。斯坦福大学的约翰-C-米切尔(John C. Mitchell)对他所看到的感到担忧:
在充满活力的创新和意想不到的发现迸发两年之后,我最大的挫败感是,包括我所在的大学在内的大多数高校都在背弃我们所学到的一切。远程工作受到严格管制。在线教学被淘汰。
长期以来为教育专家所熟知的主动式学习或掌握式学习等创新正在被淘汰,因为旧习惯的回归太容易了。转型已不再是词汇。最重要的是,大学领导们没有做出广泛的努力来整理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或利用我们在大流行病中获得的机智、智慧、同理心和理解力。
这就好像我们花了两年时间为一个新的未来打下基础,却因为一个普遍需要重塑的系统所带来的熟悉的不适而放弃了它。
在米切尔所在的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大流行期间取消了期末考试,但第二年又恢复了考试;大流行期间增加了定期的小测验,即"概念检查",但后来又停止了;大流行期间实行了修改和重新提交政策,但后来又停止了。
很难找到一所宣布永久性转向更多在线或异步教学的传统面授学院,也很难找到一所决定减少对校舍依赖的实体校园。大流行病期间对教学日历所做的大部分修改--夏季课程或学期划分--都被推翻了。学生们又开始参加分级考试。新官上任三把火。
传统学院更倾向于将大流行时期视为一种中断,而非永久性的方向转变。
即使存在种种缺陷,高等教育还是利大于弊,它开展了许多有效的实践活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但是,如果高等教育愿意认真思考转型变革,更不用说启动变革,如果高等教育愿意像审视其课程中的许多学科一样认真审视自身的工作方式,那么高等教育就能更持续地为更多人带来更多益处,避免许多机构的未来越来越暗淡。
业界似乎既承认又忽视了这一现实。Inside Higher Education 对 2023 年高校校长的调查令人大跌眼镜。近80% 的人认为,他们所在的院校在未来十年内将保持财务稳定,与此同时,72%的人认为,他们所在的"院校需要在商业模式、课程设置和其他运营方面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人们认为大学是不能容忍保守观点的地方,这对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59%的人认为"公众对高等教育可负担性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威胁似乎无处不在,但在他们自己的校园里却存在。研究和教授高等教育的凯文-R-麦克卢尔(Kevin R. McClure)有些温和地指出,这些校长"也许更多的是在希望而不是战略上运作"。
里克-斯泰斯洛夫(Rick Staisloff)的公司为数十所高校提供咨询服务,他对调查结果表示担忧:"如果这里所表达的观点是真实的,那么高等教育就可以继续按照现在的方式做下去。... ......
我不会建议当今美国的任何一位校长将他们目前的模式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保罗-N-弗里加(Paul N. Friga)也为许多这样的学院提供咨询,他有些困惑地指出,"似乎仍然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们将以某种方式勉强度日'"。
对于其中的一些院校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悲哀但恰当的墓志铭。
本文改编自《无论如何,我都反对》(Whatever It Is, I'm Against It: 高等教育中的变革阻力》,本月由哈佛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