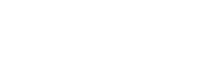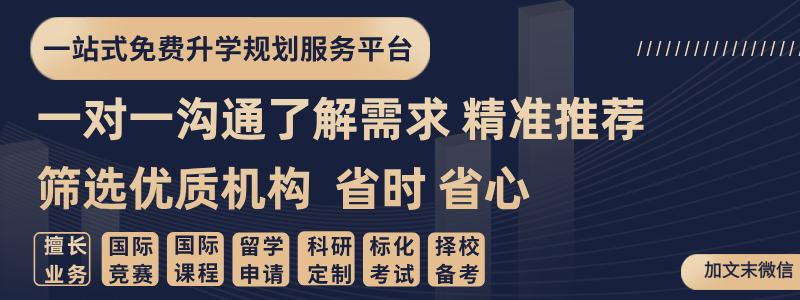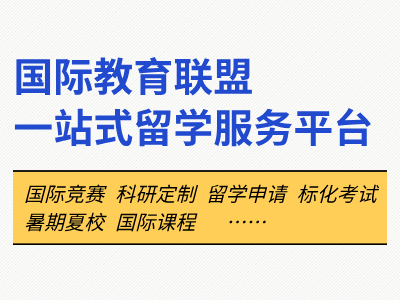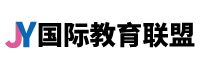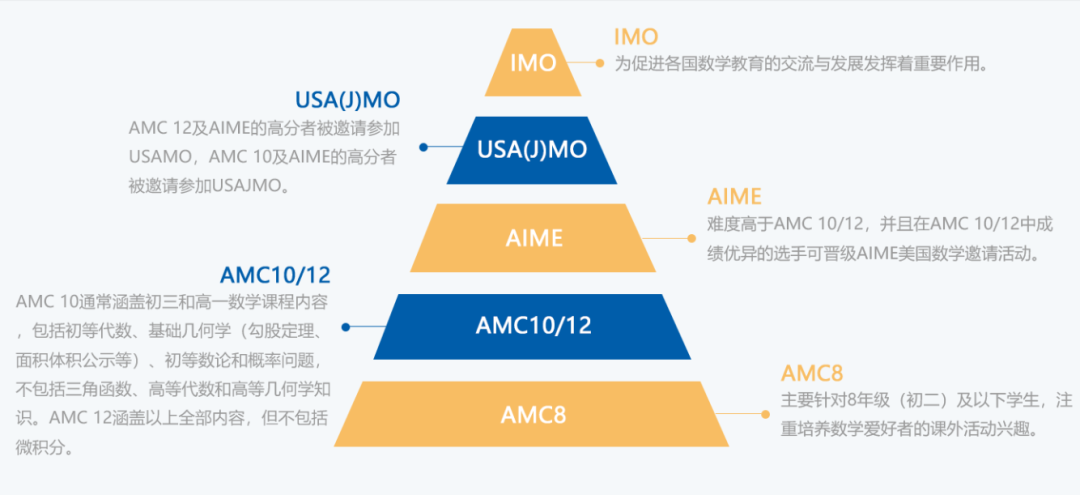美国TASS(全名:Telluride Association Summer Seminars;原名TASP)被公认为人文领域的顶级夏校,以其高含金量和高选拔性著称,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最难申请的人文类夏校。
24届的TASS项目即将于2024年1月4日截止,近日在协助学生准备TASS申请的时候,老师看到一篇关于22夏季TASS项目的博客,其内容是一名黑人教授讲述自己在该项目授课时被学生认为是种族主义者,最终该课程因为政治争议问题被迫提前停止。
想来有意向申请TASS的同学应该对此类话题颇有兴趣,故编译了这位教授的原文供大家思考学习。
作者信息
姓名:Vincent Lloyd
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教授
政治神学研究中心主任
《Black Dignity: The Struggle Against Domination》作者

▲原标题:一位黑人教授,被困在反种族歧视者的地狱里。原文发表于2023年2月10日。
研讨会(Seminar)第一天时阳光明媚,我和一群紧张而兴奋的17岁少年们坐在野餐桌边。12名高中生被泰留瑞德协会(Telluride Association)通过严格的申请程序选拔出来(据报道录取率约为3%)一起参加为期六周的大学级别的课程,该项目所有费用都已由协会承担。
这个团体让我想起了我给女儿读的《本尼迪特天才秘社》书中的英雄:在这些为了一个共同的项目而聚集在一起的青少年之中,每个人都有非凡的能力和一些怪癖。一个来自加州的女孩以机关枪一般的速度说话和思考,并在疫情期间开始收集宠物蜗牛,现在她有100多只蜗牛了。一个来自中国省立学校的女孩虽然从未去过美国,却掌握了不带口音的英语,并非常热爱E.M. Forster的作品。除了参与研讨会,学生们还实行民主自治:他们住在一起,并且制定自己的规则。在最初的几天,学生们正如所期待的那样,时而活泼,时而拘谨,所有人都好奇、有趣,尝试与他人、与研讨会的内容建立联系。
四周后,我再次坐在聚集的学生们面前。现在,他们的表情冷漠,眼睛无神。从第一周开始,我没有再看到一个人的微笑。他们的人数减少了两个:前一周,他们投票将两个同学赶出了研讨会。而我将是下一个。
每个学生都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内容是关于研讨会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延续了针对黑人的暴力、黑人学生如何受到伤害、我如何对无数次微小的侵犯负有罪责(包括通过我的肢体语言),以及学生如何因为我没有立即纠正那些未能将歧视黑人视为世界所有问题的原因的观点而感到不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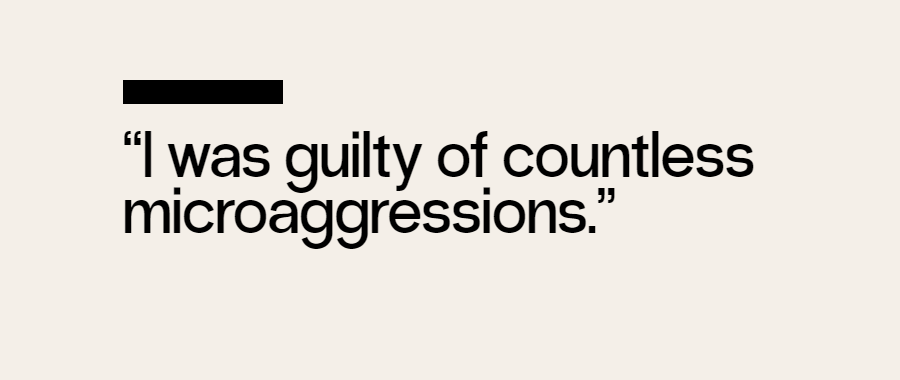
这可能只是对校园“觉醒”文化和传统教育美德丧失的又一次哀叹。然而,我们的研讨会主题是“美国的种族和法律界限”。我们6周的研讨会中,有4周的主题是关于反黑人的种族主义(另外两周则在关注反移民和反原住民的种族主义)。我是一名黑人教授,主管我大学的黑人研究项目,领导着反对种族主义和倡导转型正义的工作坊,出版了关于反黑人种族主义和废除监狱的书籍。我住在费城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我的女儿在一所以非裔文化为中心的学校上学,另外我是当地黑人文化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像其他左翼人士一样,我曾经对针对当前美国对种族问题讨论的批评不屑一顾。但现在,我的思绪转到了1970年代的那个时刻,当时左翼组织崩溃了,对匹配和提高自己同志的战斗性的需要导致了一种充满教条主义和幻灭感的有毒文化。一群精神焕发的高中生怎么也会这样?

泰留瑞德协会(Telluride Association)常年来一直保持低调,即使在高等教育界也是如此,但它在塑造美国精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校友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酷儿理论家Eve Sedgewick和后殖民理论家Gayatri Spivak(为协会第一位女性成员)、佐治亚州政治家Stacey Abrams和记者Walter Isaacson、新保守派的Paul Wolfowitz和Francis Fukuyama(其曾在协会的董事会任职)。1911年,矿业企业家L.L. Nunn在创建深泉学院的几年前创办了这一协会,它的目标是在高中生和大学生中培养民主的社群。它在康奈尔大学和密歇根大学附近有学术基地,学生在这里获得奖学金,实行自治,并将学术生活和服务性工作融入他们自己的集体生活。1954年,泰留瑞德协会开始了它的高中生暑期项目。
多年来,许多美国顶尖大学的教师都曾为该项目授课。课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共产主义和民主制度的理念冲突”是在1956年讲授的;哲学家Robert Nozick在1965年讲授了“自由的哲学概念”,而最近几年的主题包括“凯尔特人和维京人的神和英雄”、“数字世界中的公共诗歌”、“安全国家的文学”和“自由之夏”。
2014年,我在泰留瑞德的康奈尔校区教过“种族和法律的界限”。最初的几天和我在2022年研讨会一模一样:学生们都拥有着过人的能力;他们会问一些试探性的问题;他们有时也会很尴尬。然后,随着六个星期的过去,我可以看到学生们彼此之间以及与我之间形成了纽带,我可以看到他们对课程的付出与努力。他们总是准时出现并完成好作业。研讨会期间,我女儿刚满1岁,由于我们在镇上谁也不认识,我们还邀请了学生们到我们住的房子里参加她的生日聚会。
六年后,我偶然发现了泰留瑞德的网站,并惊讶地在首页看到了我在生日聚会上的照片。带着这些美好的回忆——以及由于在全美国的相关讨论因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之后,重新探讨有关种族的棘手问题的可能性让我兴奋不已——我联系了泰留瑞德,希望再次教授这个研讨会。(协会的研讨会是共同讲授的,我的研讨会是和我妻子合作开设的,她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原住民研究的教授。)
在George Floyd之死引发的抗议之后,一群黑人校友向泰留瑞德协会施压,要求检讨种族主义——他们声称,种族主义已经融入了协会的文化。他们的公开信说:“我们都经历了协会内部和其项目中对黑人的歧视”。结果,夏季的研讨会项目被重新设计:现在只提供“批判性黑人研究”和“反压迫研究”的研讨会。前者将“寻求更具体地关注黑人学生的需求和兴趣。”而我的研讨会“种族和法律的界限”属于后者的研究范畴。
泰留瑞德项目在演变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追寻自由价值观的传统。它从1950年代就已开始提供种族相关的课程,其康奈尔校区在1970年代被称为“校园中最自由的小群体”,因为它相对较早地接受了犹太人、黑人和女性学生。1993年,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鼎盛时期,协会开始提供一系列新的研讨会,重点关注种族和差异,面向未被充分代表的学生。但是我的Telluride研讨会内部分歧导致的最终破裂正表明了,这种围绕黑人性(blackness)展开的、不断诱惑着美国精英阶层(尤其是精英教育机构)的在平权征程上的最后一步,我们走得太快了,甚至是走入了缺乏条理的自相矛盾,或更糟糕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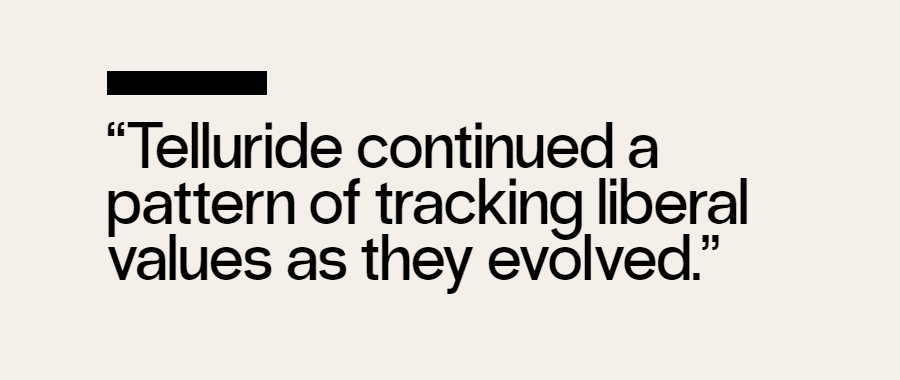
在康奈尔校区,学生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并同时参加两个不同的研讨会。2014年,两个研讨会小组的参与者在研讨会之外共同生活,探索伊萨卡镇和康奈尔大学的校园,一起吃饭和欢笑,并建立了一个系统来共同治理他们的集体。然而,在2022年,我被告知“批判性黑人研究”的学生将单独生活和学习,以创造一个完全的“黑人空间”。我的“反压迫研究”学生和他们分开了。和我预想的32名高中生一起学习生活不同,我的小组仅由12名学生组成(在“哗变”后减少到9人)。
此外,在2022年的项目中,下午和晚上将不再用于娱乐和做作业。两个大学生被称做“家务总管”并被分配去创办反种族主义工作坊(Workshop),以填补下午的时间(其中一名领导的人将被我叫做Keisha)。这些Workshop有关于白人至上主义、特权、非洲独立运动、Angela Davis思想和行动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最开始为期一天的“转型正义”Workshop之后举行的。这些Workshop迫使高中生面对棘手的问题,并以他们从未被挑战过的方式接受挑战,最终使这些学生们身心俱疲。
我对反种族主义Workshop并不陌生,我参加过许多这样的活动,我自己也主持过这类活动。但是这里的Workshop是由两个大学生组织的,充满了时代精神。从我收集到的信息来看,无论这些Workshop表面上是关于什么主题,它们涉及到粗糙地传达某些教条式的主张:
●经历苦难传达着权威。
●压迫没有等级之分——除了针对黑人的压迫,它自成一类。
●相信黑人女性。
●监狱永远不是答案。
●黑人需要“黑人的空间”。
●联盟通常是行动性的。
●所有非黑人,还有很多黑人本身,都有反黑人的罪责。
●没有办法避免对黑人的歧视。
研讨会(Seminar)的形式与反种族主义工作坊(Workshop)的形式相反,协会试图同时拥有这两种形式。从本质上讲,研讨会需要耐心。日复一日,每个发言在另一个发言基础上继续拓展,因为一个学生会注意到另一个学生忽略的东西,同时教授会将讨论引向最重要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基于文本:文本中的特定单词、短语、论点和图像为对话提供了必要的争议之处,让参与者能够讨论具体的事情。导师将会温和地(理想情况下,应该是几乎看不见地)引导讨论向重要的方向发展。
研讨会假设每个学生都有天赋,即使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拥有不同数量和种类的知识,以及不同的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我们利用我们不同的洞察力一次又一次地互相推动着讨论前进,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达到最好的状态。当这种实践是由精心选择的文本(不仅仅是“伟大的书籍”,而是那些在探索至关重要的问题时能够挑战我们的文本)引起时,研讨会就成功了。
这需要时间。第一天,你会很沮丧。第二天和第三天,你会很沮丧。即使在最后一天,你也会感到沮丧,尽管理想情况下,你的沮丧可能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研讨会上的每一次干预发言都是不完整的,也可能会把事情搞砸。后来的每一次也会是不完整的,也依然会出错。但是这个过程中会迸发很多见解和惊喜,因为每个参与者用会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文本。
我很想加上一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民主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片面的知识。我们每个人都会一次又一次地犯错。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通过相互倾听、补充和挑战同伴的见解来加入这场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几年来,几十年来,我们共同的方向是正义和真理。
如果说研讨会(Seminar)是慢餐,那么由大学生举办的反种族主义工作坊(Workshop)则像是进食含糖食物过多后的兴奋。在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场所,所有的标签都浓缩、打包和传递。最糟糕的反种族主义Workshop只是为参与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回应方式——大声转发。

泰留瑞德的学生体验了两种与同伴一起学习的方式,也体验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从最初的“转型正义”工作坊(Workshop)开始,学生们学会了在同意同学的话时打响指。这种做法立即进入了研讨会(Seminar),并且被武器化。一个学生会尝试发表一个有争议的,或者只是不寻常的观点。沉默。然后另一个学生会重复一条反种族主义的教条,房间里就会充满打响指的声音。
在2014年研讨会的第一周,针对奴隶制话题,一名华裔美国学生指出了我们课文中白人奴隶主为被奴役者提供食物的一个时期,并表示这表明奴隶制的两面性。在我想办法把他的发言变成更复杂的讨论的垫脚石之前,两个学生提出了文本中的其他证据,表明奴隶制是一种道德上令人憎恶的东西,并不值得进行两面性讨论。最初的那位学生,一开始看起来他似乎有种摇摆不定的道德标准,而在研讨会结束时,他表达了一种新的对待正义的信仰。
在2022年的反种族主义工作坊(Workshop)上,非黑人学生知道他们需要以黑人的声音为中心——并且学会闭嘴。Keisha报告说,这对亚裔美国人学生来说尤其困难,但他们正在努力。(最终,两名亚裔美国学生被开除出这个项目,而其原因Keisha说不能告诉我。)这对研讨会的影响是迅速而显著的。在第一周,参与情况如你所料:有两三个害羞的学生只在搭档或小组活动中发言,两三个直言不讳的学生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其余的则介于两者之间。黑人学生一个直言不讳,一个居中,一个腼腆。到了研讨会的第二周,两个白人学生在实际意义上沉默了。亚裔学生中有两人仍然活跃(正是即将被开除的两人),但绝大多数发言来自三名黑人学生。两个酷儿(Queer)学生(一个亚裔、一个白人)完全沉默。黑人学生基于自身和其家庭的经历,有很多的有趣的想法想要表达,但当多种观点相互碰撞、相互斗争并发展时,研讨会(Seminar)才是成功的——而这在这期项目中变得不可能了。
在他们的“转型正义”工作坊(Workshop)上,我的学生们学会了关于“harms”(伤害)的理论。这个名词,以及它所表达的思想框架,来自于废除监狱运动。其支持者鼓励我们思考伤害以及如何纠正伤害,而不是将罪行与惩罚相匹配。他们通常通过邀请更广泛的群体参与来辨别伤害的影响、产生伤害的原因以及未来前进的道路。在反种族主义Workshop的讨论中,伤害是指任何让你感觉不太对劲的事情。对于一个17岁的人来说,在一个高度选拔性的、费用已被免除的夏季项目中,新学习了“伤害”这种概念,可实践这种理论框架的场景是相对较少的。我的研讨会成了试验和武器化这个名词的场所。
在我们讨论监禁时,一名亚裔美国人学生引用了联邦囚犯的人口统计数据:大约60%的被监禁者是白人。黑人学生说他们受到了伤害。他们在一次Workshop上了解到,“客观事实”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工具。我被告知,在研讨会(Seminar)之外,黑人学生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纠正他们因听到与黑人无关的监狱统计数据而受到的伤害。几天后,这名亚裔学生被该项目开除。类似地,在进行了一周关于美国原住民遭受的可怕暴力、死亡和剥夺的讨论后,Keisha向我报告说,黑人学生和他们的盟友受到了伤害,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关注对黑人的伤害。当我试图解释,教学大纲上已经指出了,我们即将有四个星期的时间集中在对黑人的歧视问题上时,Keisha则说伤害问题是紧迫的,需要立即解决这个问题。

在最近的一本书中,John McWhorter断言,“反种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我很快反对了这个想法。去年夏天,我发现,“反种族主义”是对宗教的曲解,其更像是一种邪教崇拜。从《异狂国度》到Nxivm组织,邪教的特征在流行文化中变得被人熟知。睡眠不足、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时间感崩溃,一切与崇拜有关的事情都变得极其紧迫、参与者在情感上备受打击。在这种被削弱的状态下,参与者了解并坚持教条式的信仰。而任何外来者都会成为威胁。
这个夏季项目的12个参与者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一起,我几乎是他们遇到的唯一一个局外人,我被标记为一个威胁。
我的故事中似乎缺少了一个邪教的特征: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强制追随者与世界分离,制造情感脆弱性,并植入教条。这时Keisha登场了。Keisha最近从一所常春藤大学毕业,得到了一位在电视上很活跃的黑人知识分子的指导。Keisha介绍自己是一名黑人女性,出身贫寒,祖母的四肢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打断。她大学期间还在监狱里教了四年书,倡导废除监狱制度。她告诉全班同学,她主修黑人研究,受到了黑人女权主义者的培养(尽管她著名的导师是男性),她打算用自己的一生将学术界朝着黑人正义的方向转变。
泰留瑞德协会让Keisha在我的班上担任助教,并在下午为学生们组织工作坊(Workshop)。我欢迎Keisha进入课堂,并且建议可以找些日子让她来主持讨论或分享她自己的研究。然而相反的是,在最初的三个星期里,她在课堂上基本上保持沉默,在下午的Workshop上则对研讨会进行逆向安排。在为期一周的关于美国移民体系中的种族主义背景的课程中,Keisha发现我们的一本书(亚裔美国人的回忆录《Nisei Daughter》)不够激进,所以那天下午她向学生们讲述了更激进的河内山百合(Yuri Kochiyama)的作品。让Keisha感到沮丧的是,我们的讨论监禁的那周是从George Jackson开始的,而不是一个黑人女权主义者,所以那天下午她讲了关于Angela Davis的课。我与她和全班同学详细讨论了学习随时间推移而展开的情况,讨论了在进入下一个想法之前与一个想法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以及课程的总体方向,但对她来说(很快对学生来说),他们没有等待思想层层递进迭代的耐心。
Keisha和我按理说应该每周见面,但她告诉我她不能提前约好时间,她会让我知道她什么时候有空。事实上她从来没有和我约见面。但是,当学生感觉受到“伤害”时,Keisha确实会抽出时间进行干预。在一次课堂上,当我们讨论“布朗案”时,另一位老师解释了什么是为最高法院的决定提供心理学依据的“娃娃测试”——给孩子们看黑色或白色的娃娃,并询问他们会用什么语言来描述它们,“有色”、“白色”或“黑色(negro)”。在研讨会休息时,一名学生向Keisha报告了这一情况,她冲进来告诉我们,一名学生因听到“negro”一词而受到伤害。
研讨会的第四周研究了反黑人的理论。应该可以预料到,研讨会将在那一周爆发:从研讨会的第一天起,Keisha就一直在谈论反黑人在性质上比任何其他压迫制度都更糟糕,所以她希望我们停留在那周的讨论,无法继续推进是可以预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反黑人话题成为了这节课的高潮与至暗时刻)。冲突爆发在这讨论反黑人理论周的最后一天,我邀请学生们来我家,我们在那里谈论了几个小时的阅读材料(选自Frank Wilderson的《非裔悲观主义》),然后我们共进晚餐。到这个时候,学生们的脸永远阴沉着——至少当Keisha在房间里的时候是这样。偶尔,在一对一的交流中,我仍然可以和他们开玩笑,或者听他们谈论青少年生活中的琐事。
当我坐在后院的草地上开始研讨会时,Keisha打断了我:“我认为你应该以讲座形式讲述这篇文章的背景,告诉我们要点。”我提醒全班同学研讨会的形式、这么设置的原因,我们一起阅读和讨论理论,并探索研讨会的价值。Keisha坚持说我需要做一次讲座——马上。最终,我同意了。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讨论了Wilderson令人回味的文字,富有成果,然后我向学生指出,“我在最初的讲座部分中提到的所有内容,我原本都会在研讨会上提到。每天,我都试图在研讨会中插入相关的背景信息,并在简短的发言中强调关键点,以便研讨会可以由你们的问题来引导。关于Wilderson,我可以做几十场讲座,每场讲座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这篇文章,但我想要的是与你们分享你们想要的信息,与你们带来的见解进行对话。”
我的评论使Keisha被“点爆”了。她发表了长篇大论,说我是如何无视一名黑人女性的要求,以及我是如何让这个地方对黑人学生来说不安全的。然后她宣布,她会把学生带回他们的房子,而不吃我为他们准备的午餐。
我很清楚情况正在失控,在学生们离开我家后,我联系了泰留瑞德协会来分享我的担忧。他们答应进行调查。周日晚些时候,我被告知学生们因为太累了,周一无法上课。星期二早上,没有人出现在研讨会的教室。我等了10分钟,Keisha进来了。她说学生们有话要对我说。又是十分钟的沉默等待。然后剩下的九个学生都进来了,每个人都拿着一张纸。他们接力式的每人读了一段。从他们嘴里说出了Keisha在课后与我的“紧急”会议上对我说的一切,当时学生据称受到了伤害。学生们知晓所有反种族主义的教条,但在他们的世界里并没有真正的种族主义可供批评,Keisha引导了所有学生在我身上进行反对种族主义战斗的愿望。
他们声称:我使用了种族主义的语言。我弄错了Brittney Griner的性别。我曾多次混淆两个黑人学生的名字。我的肢体语言伤害了他们。当(现在已经被开除的)学生在课堂上对其他同学造成伤害时,我没有纠正它们。当只有一方是正确的时候,我邀请他们思考争论双方的论证观点。学生们最后提出了一个要求:鉴于他们所遭受的伤害,如果我放弃研讨会的形式,改为每天讲授内容,纠正他们中任何质疑正统观念的人,他们才能继续上课。他们声称,他们在夏天收到的唯一的批判性视角来自Keisha。那个有很多蜗牛的白人女孩强调了他们的观点:“Keisha代表了我:她说的一切都比我自己能表达的更好。”
Keisha在表演她的角色方面有独特的天赋,但她不是这部剧的作者。将反种族主义推向极限,我们达到的不仅仅是空洞的教义,而是滥用:这种病态的关系将我们与世界隔绝,与那些理性的互谅互让隔绝,与在这个世界中组成生命的情感隔绝。我们在我遇到的悖论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这一项目本应围绕“转型正义”而不是惩罚性模式来组织,但这个群体却设法驱逐了两名成员。学生们不断表达他们寻找实际行动来帮助改变世界的愿望,但四周后,他们学会了说反对黑人这一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世界永远无法改变。学生们想要自由,为了他们自己和所有人,但是他们开始说通往自由的唯一途径是灌输教育:让我告诉他们该思考什么。
对我来说,最难过的是听到黑人学生说的话。他们称需要额外的帮助,他们正在努力理解阅读材料中的内容,除非有指导,否则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问什么问题。首先是Keisha说了这些,然后是黑人学生开始这么说,然后他们的“盟友”为了声援他们重复了这个观点。但我目睹了他们的学习。我听到他们对难懂的课文提出批评性的问题。我看到他们的写作进步了。我看到他们能够用深思熟虑的方式使用复杂的概念。他们只是不相信自己。
在研讨会的第一周,我注意到有两三名学生相对害羞(一名黑人、一名亚裔和一名白人),于是我问Keisha,她对如何让他们更充分地参与进来有什么建议。她说,她认为学生们不参与是因为他们觉得研讨会上讨论的问题与他们无关。几周过去了,越来越少的学生上交了书面阅读反馈,越来越少的学生准时出现。他们在课堂上睡着,他们会在课间出去吃零食。如果我们把研讨会这种形式理解为当你喜欢它时就进入,只要你的观念不受质疑就留在里面,当你感到不舒服时就可以离开,那么研讨会这种形式就不能在泰留瑞德的项目或大学里持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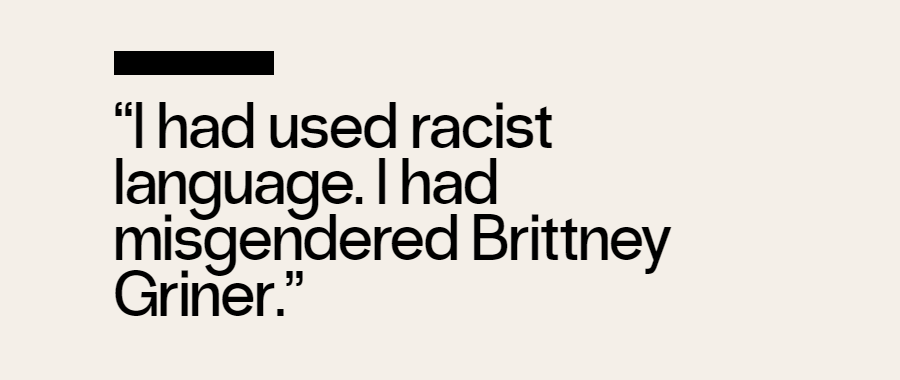
在学生们提出他们的抱怨和要求后,我告诉他们我需要时间来思考。这个项目被迫终止。我决定,继续下去的唯一方式是泰留瑞德的领导层进行干预。我提醒学生们,这个研讨会是一个更大的组织的一部分,这个组织有其价值观和规范。我是签了合同来教授一个大学级别难度的研讨会,而我按照这个概念的一般意义来理解它。
泰留瑞德协会由项目校友管理和运营,他们自愿贡献自己的时间来推进协会的目标。监督夏季项目的志愿者向我解释说,在松散、庞大的泰留瑞德世界中,对夏季项目的方向存在内部分歧,世界的一些角落狂热地追求将分析反黑人作为唯一的焦点,其他角落希望继续举办系列研讨会,就像过去一样。他们意识到这个夏天不仅仅是在我们的研讨会上,而是在整个协会的项目中都充满了坎坷,因为协会希望尊重学生集体的民主自治,领导层不愿意干预。如果环境太恶劣而无法继续,我可以暂停研讨会,提供几次以我作为“特邀演讲者”的会议,不再继续研讨会这种形式。
我给学生和Keisha发了电子邮件,告知他们这个决定,并承诺我将会阅读和回复学生们写的任何书面作品——但我从未收到回复。没人发书面作业给我,也没有人表示希望参加一个我将作为“特邀演讲者”的会议。学生们还有将近两周的时间,但是研讨会取消了,他们回家了吗?他们告诉父母了吗?Keisha一整天都在给他们讲课吗?我不知道。我已经从这一虐待关系中解脱出来,但九名学生仍然被囚禁在其中。对民主的信仰使得虐待被允许了,而且没有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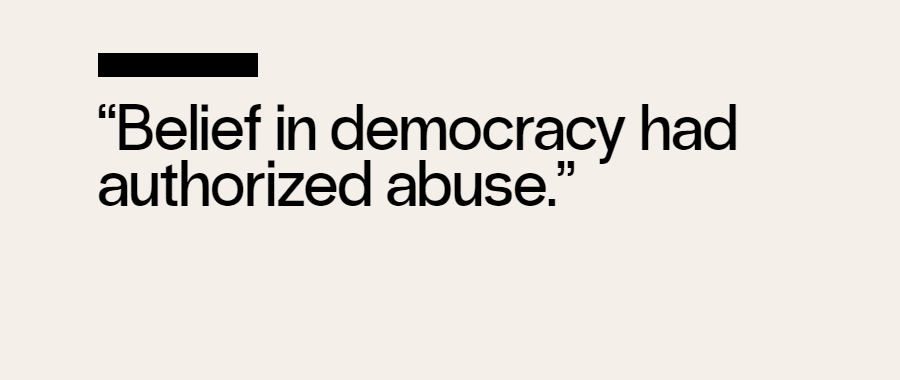
至少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没有。但是三个已经离开的学生(两个被开除,一个有签证问题)单独联系了我。他们想做阅读,他们想写论文。他们想在网络上和我见面,继续研讨会。所以我们继续以另一种形式开展研讨会,这是一个流亡研讨会,阅读黑人思想的经典(C.L.R. James, Charles Chesnutt, Harriet Jacobs, James和Grace Lee Boggs),他们是民主的信徒,民主的逃亡者。